刘贵祥,甘肃文县人,天水师范学院1997届校友。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天水师专政教系(辅修法律)学习。2004年获兰州大学哲学硕士学位,2011年获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曾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。现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及学科带头人。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,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评审专家、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、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》编委等。目前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共10多项,出版代表性专著 1部,完成译著两部。在《马克思主义研究》《世界哲学》《现代哲学》等核心期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(含译文)40多篇,多篇被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转载、摘录。教学、科研成果获省部级、国家级学会奖等共10余项。
子曰:五十而知天命。一晃自己已到五十岁,当有机会蓦然回首,离上大学已经30年之久了。30年离自己如此之远,但似乎又如此之近。每当回想起母校学习的点点滴滴,学校那些鲜活的人、物、事如在昨日,总是伴随个人的发展,与个人的追求一起交织前行。
1994年秋我进入天水师专学习,被录取到当时的政教系,也就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。我们入学时它有两个专业,一个是思政教育辅修法律,另一个是思政教育辅修历史,大家简称政法班和政史班。我们入学时学校已经搬迁到现在所在的新校址,校园面积虽然不大,但是校园规整而紧凑。教学区和活动区主要集中在今天的东校门和正德路之间,学生的宿舍楼主要有两栋。宿舍楼西北是一栋综合教学楼和行政楼,今天都已经改造成学生宿舍;西南则是田径场、篮球场和图书馆等。校区不大但两边绿植成行,春夏花开时节非常漂亮。
也许是高考以后的重压解除,也许和所有20岁上下的青年一样,我当时除了学习就爱参加体育活动,其中最爱的又是打篮球。当时的田径场和篮球场都还没有硬化,没有现在的塑胶跑道和塑胶场地。但是,细沙铺底的跑道和尘土飞扬的篮球场,并不能阻止大家锻炼和参加比赛的热情。每天早上要出操,先是围绕着东区体育场跑步,然后以班级为单位做广播体操。像我这种篮球爱好者,常规体育活动以外,还参加系上和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。当时最热烈的恐怕要算中午的篮球赛,那时校东门餐厅对面就是篮球场。如果那天碰上班级之间有比赛,其他人刚好打完饭走出食堂,大家会边吃饭边看比赛,吃饭的有时会忘情地大声呐喊,吃完饭的则会敲着饭盒助威,气氛真是独特而热烈。真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独有的热情和激情!如果学校的各种体育活动主要锻炼了我们的体魄,那么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则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精神食粮。

(1995年政法班的篮球队,后排左二为作者)
当时有三件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后来的道路和选择。第一件事是学校和系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为我们后来的选择提供了更多契机。中国是在十四大(1992年)才正式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影响到了教育系统,天水师专也是在市场机制的大背景下,摸索自己更宽广的学生培养模式。其中一种新的尝试就是探索“非师范类”专业的培养,我们入学时“思政教育+辅修法律”就属于这样的新模式。这种新模式当时恐怕只是一种多样化的探索,但我们因为学了法律课程,很多人自然参加当时的法律本科自学考试。后来,从我们九四政法班毕业后的情况来看,相当一部分同学最后都去了政法系统工作,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探索的另一种开花结果。就我个人来说,我在校时也参加了法律的自考,在毕业后不到两年,在考完了法学的15门课程后,就顺利拿到兰大法律系的本科文凭。
这种与时俱进的探索,与另两件事被证明是有远见的。一个是我们刚入学,师专就设了一个“四级英语”学习班。就是把当时全校高考英语在90分(满分150分)以上的学生,单独编班并配最好的英语老师,让我们去考四级英语,这在当时还是新个事物。仅就这一点,就让我的英语一直没丢。值得自豪的是,在1999年第一次准备报考兰大研究生的时候,一次我在学英语时发现了一个翻译问题,就顺便写了一个小文章投到《大学英语》,没想到这篇“一对矛盾翻译之我见”的小文章,不但很快被发表,而且还挣了一小笔稿费。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00多元,小小的稿费对我当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奖励,更为重要的则是我收获了一种学习能力上的自信。这种外语学习能力的自信很重要,它甚至一直延续到2015年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参加出国外语考试,2017-2018年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出国访学,等等。

(2018年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)
另一个事就是我们碰上了系里的一批好老师。当时有三个老师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学术影响,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之路。首先是我们的班主任雍际春老师,雍老师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陇右历史的名家。我记得当时报栏公布的老师研究成果,雍老师常常是名列榜首。雍老师还长期担任天水师院“陇右文化研究中心”的主任,去年还担任国际伏羲文化大典的解说嘉宾,足见他历史研究方面的水平。另一位是直接影响了我后来考研方向的高学文老师。高老师讲授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,这门课不好讲,但是他则讲得生动有趣。我记得他讲具体科学和哲学的关系,用洋芋和粉条打比方,说“理论化具体化的洋芋就是粉条”,这就把抽象的东西一下具象化了。此外,高老师在教学时还穿插一些马列原著知识,这在当时是最难得的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在地摊上淘了一本《反杜林论》自学,而他带有研究性质的讲授,则激起了我潜在的哲学研究的兴趣。这种兴趣让我后来在考研时最终选择了哲学而放弃了法学。第三位老师是吴卫东老师,他当时给我们开设伦理学的课程,吴老师上课知识渊博,他的声音和形象具有一种磁力,这构成他个人独特的气质和魅力,每次给我的印象总是如沐春风。以致于我们在师专期间,就觉得将来当老师的话,我们的形象应该像他那样才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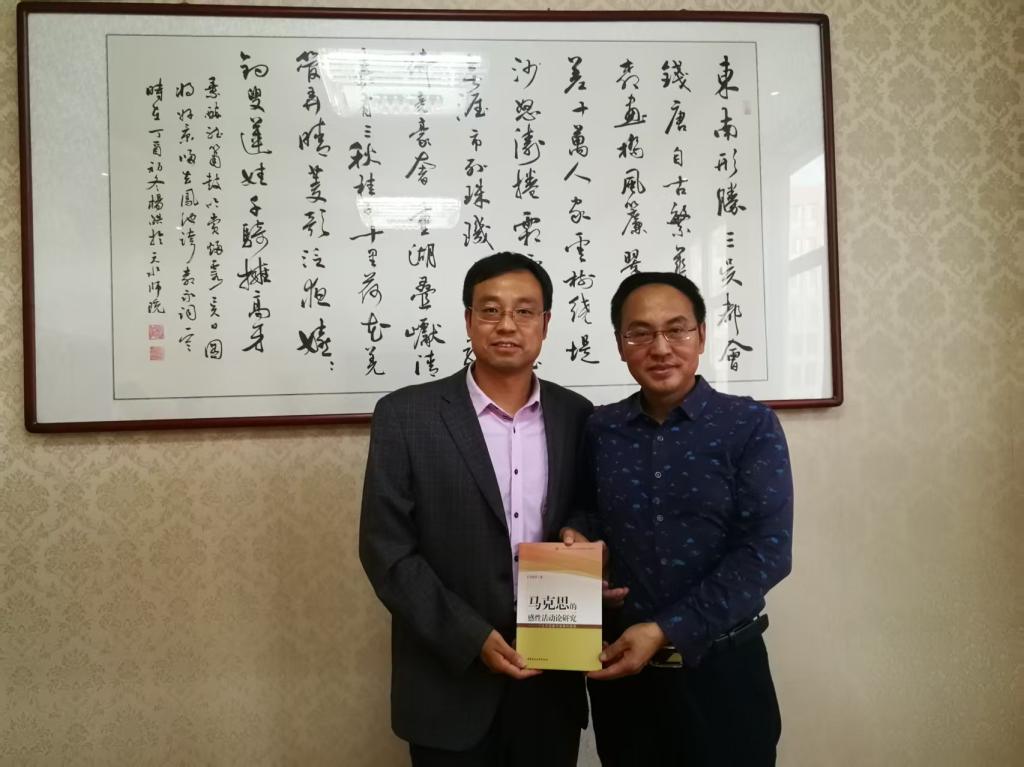
(向母校图书馆赠书,右为吴卫东教授)
简言之,学校拓展辅修法律专业和设置英语提高班,加上系上老师各有所长的教学,这三件事情,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考研方向和道路。现在想来,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“你如何开端,将如何保持”那样,30年前的母校和政教系,虽然那时的规模还不大,但是很多优秀教师的集中,为我们后来的发展播下了最初的种子。
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回望母校发展的66年,她已经实现了从师专到师院,从师院到师大的大发展,这每一步都凝聚着母校人无数的共同努力。作为母校的一名学子,在此,也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,学子越来越强!
 甘公网安备 62050202000257号
陇ICP备15003457号
甘公网安备 62050202000257号
陇ICP备15003457号





